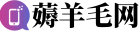傍晚——当你头上出现第一根白发
麦穗
现代
额顶,亮起第一颗星星
划过去,在乌黑的天际
留一痕银丝,流星
流过城郭,流过田野
流过群峰,流过涛尖
——穿起一串岁月
遥远处一抹霞光将淡去
将淡去一天的太阳、西沉
隐退了,峦峦的山的壮硕
林林的树的坚挺
迎四周垂落的幕
幕
隔绝了所有的声和色的缤纷
掌声转了向
泪眼也转了向
寂寞在幕帷上开始显现
星,一一地升起
一颗,二颗……
在额顶聚成一片银河
伐木迹地
麦穗
现代
使我想起大屠杀
步入伐木后的迹地
一片狼藉的残枝断木
虽不见血流成河
也不闻哭泣惨号
眼前成千上万个带着
刀痕斧迹的根株
不就是一个个被残害的
生命
一场世纪的浩劫
刚在这里落幕
残破的树的肢体
并非没有血和泪
是已被山吸尽
不久
它们将化成愤怒的洪涛
在山底下淹没田庄和城镇
傍晚——当你头上出现第一根白发
麦穗
现代
额顶,亮起第一颗星星
划过去,在乌黑的天际
留一痕银丝,流星
流过城郭,流过田野
流过群峰,流过涛尖
——穿起一串岁月
遥远处一抹霞光将淡去
将淡去一天的太阳、西沉
隐退了,峦峦的山的壮硕
林林的树的坚挺
迎四周垂落的幕
幕
隔绝了所有的声和色的缤纷
掌声转了向
泪眼也转了向
寂寞在幕帷上开始显现
星,一一地升起
一颗,二颗……
在额顶聚成一片银河
伐木迹地
麦穗
现代
使我想起大屠杀
步入伐木后的迹地
一片狼藉的残枝断木
虽不见血流成河
也不闻哭泣惨号
眼前成千上万个带着
刀痕斧迹的根株
不就是一个个被残害的
生命
一场世纪的浩劫
刚在这里落幕
残破的树的肢体
并非没有血和泪
是已被山吸尽
不久
它们将化成愤怒的洪涛
在山底下淹没田庄和城镇
灵感
麦穗
现代
灵感之鸟飞进了心窝
久久回绕似久别重逢
他的来临使我沮丧和焦虑
因为我的心田荒如沙漠
使美丽的鸟儿无法栖落
当我发觉鸟儿已离去时
才后悔没有早些种植绿树
徒使千万只灵感之鸟
飞临我这荒芜的心田
也难唱出一曲悦耳的歌
酒
麦穗
现代
怀乡的时候就会怀念你们
那些拥有诗样标题
散文般内容的
花雕、竹叶青、女儿红……
每当我喃喃地念着
你们醇醇的名字时
红就爬上了双颊
让我沉醉在浓浓的
浓浓的乡愁里
灵感
麦穗
现代
灵感之鸟飞进了心窝
久久回绕似久别重逢
他的来临使我沮丧和焦虑
因为我的心田荒如沙漠
使美丽的鸟儿无法栖落
当我发觉鸟儿已离去时
才后悔没有早些种植绿树
徒使千万只灵感之鸟
飞临我这荒芜的心田
也难唱出一曲悦耳的歌
酒
麦穗
现代
怀乡的时候就会怀念你们
那些拥有诗样标题
散文般内容的
花雕、竹叶青、女儿红……
每当我喃喃地念着
你们醇醇的名字时
红就爬上了双颊
让我沉醉在浓浓的
浓浓的乡愁里
森林浩劫
麦穗
现代
数十年相依
这里原本是一片宁静
和谐和原始并存
这里的潮湿、腐浊、郁闭、阴暗
并不适合文明了的人类
是漫天烽火还是人口的压力
迫使他们闯进了这片
鱼虫鸟兽的家园
扰乱了这里所有生存者的空间
从此林间就不见往昔的安宁
树木忍着
鱼虫忍着
鸟兽们躲避着
它们忍着躲着避着
是为了继续生存
也希望彼此友善地相处
可是人类的文明和进步
却成了这里的灾祸和不幸
他们把子弹射进鹿和麂的体内
他们把毒药羼入鱼虾生活的溪水
他们把锯斧加诸生长了数千年的
老树干
处处设下陷阱
天天闻到血腥
熊和鹿成了佳肴和补品
猕猴和松鼠被关进笼子里
连小鸟们都成了换钱的商品
山溪里的鱼虾更是菜市场里的珍品
树木和溪床里的砂石
一卡车一卡车的搬离了山林
草失去了树荫的庇护
泥土失去了树根的拦护
大片阳光乘虚而入
象一把熊熊烈火
将林地焚烧得干燥龟裂
而雨水却成了匆匆的过客
因为这里已没有条件让它留连
只好夹带土着泥沙
去山下轰轰烈烈地
制造一场洪涝
千年之后
麦穗
现代
如果可以冰存起来
在千年以后解冻苏醒
再睁开眼睛看一看
经过十个世纪的变迁
世界是否仍笼罩着
你争我夺
我虞你诈的阴暗
万一不能苏醒
千万别将他哄抬成一件
价值连城的骨董
或收取高额门票
展示成一个珍希的怪物
就把他解冻成一具
有血有肉的木乃伊吧
送上解剖台去研究分析
为何走了漫长千载
还是走不出那个
自我陶醉式的南柯梦境